「伊森,你開口說話啊,我們到底是哪個環節錯了呢,為什麼德魯無法從二期孵化。」陳坤生坐在玻璃牆外撐著臉頰問。
伊森虛弱閉眼沒有要張開的意思,昨日他的肚子才開了一個大洞,因為那群生物學家想要了解存放德魯的空間是不是因為長期與穆拉薩的體液接觸而產生變化,現在他的身體就是一個置物櫃,要找什麼東西,拿著手術刀就能輕易切開觀察。
最好笑的是他們居然把剛開完刀的自己又放回這模擬空間,泡在清水中。
因為他們堅信伊森體內的植物能加速他復原,所以他才能熬過這如海浪般不斷襲來的手術。
麻藥退去後被切開的傷口疼的伊森不斷抽氣,尤其泡到水後傷口更是刺痛,有些地方甚至微微發炎,好在體內種子適時調節體內的內分泌以及修復,伊森才沒有死在這群荒唐的生物家手中。
「你不開口也沒有關係,只不過我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而已。喔對,我忘了說,唯一一顆存活下來的德魯已經被取出關鍵細胞了,你看過正在二期的德魯嗎,像雞蛋一樣脆弱的外殼敲開裡面是有著人類腦袋的畸形。」
「不……不、不……」伊森絕望的搖頭拒絕聽到這麼殘忍的事情,諷刺的是他就算瘋狂搖頭在陳坤生的眼裡也只是輕微晃動,他的掙扎就是這麼渺小可笑。
太痛苦了,伊森總會忍不住想,要是直接死去不是很好,到底為什麼要這樣折磨他。
以前放進穆拉薩的實驗體也好,德魯跟赫拉也罷,我們的性命在這群科學家眼裡輕如塵埃。
腦海中赫然閃過那棵有點傻有點笨的守護樹,他的眼睛忍不住泛紅,胸膛因激動而起伏,每每吸進肺裡的空氣都像是銳利的玻璃,疼的伊森淚流不止。
這些淚他已分不清楚是因為身體痛而流還是因為他太想念那個部落想念那時候的生活。
「伊森看我這裡,」陳坤生從一罐玻璃器皿裡挖出一團血肉模糊的肉塊展示,「你知道二期德魯的關鍵細胞就藏在大腦裡嗎,想像一下敲破頭骨的畫面然後挖出腦漿,他就在這團肉裡。」
陳坤生將肉塊從左手甩到右手又甩回左手,褲子都沾上了粘稠液體也不以為意,他就這樣盯著伊森,看他痛苦看他悲傷。
某方面來說,陳坤生酷愛這樣霸凌實驗體,將他的尊嚴喜愛的事物完全摧毀,其實這樣有好有壞,有的實驗體會因為如此而失去自我變的很好觀察有的則會失去求生意志進而衰敗死亡。
陳坤生就在賭,賭伊森到底是哪一類的人。
「憑什麼……」
壓抑又絕望的聲音脆弱到輕輕一碰就碎裂,即便如此陳坤生還是敏感捕捉,他隨即露出一抹笑,很冰冷的笑,因為伊森的聲音裡除了絕望還有怒氣,這就是他想要的結果。
「憑什麼……」到底憑什麼你們可以站在我面前剖開我的肚子、敲開我孩子的頭!
「讓我死。」伊森打從心底懇求,我已經不想看到這些,不想看到德魯赫拉被殘忍對待,為什麼不讓我死,「為什麼折磨我。」
「為什麼折磨你?」陳坤生嗤了聲像是聽到有趣的笑話,「我沒有折磨你,我只是讓你了解身為實驗體應該被怎麼對待。我讓你好吃好住你怎麼回應我的,難道就我們頂著進度壓力然後把你當皇上伺候?不可能的伊森,你何時才能了解我們坐在同一條船上,我們一翻船你也跟著完了,我們沒有進度你自然也不會好過到哪去,所以伊森,這是你自作自受。」
許是想說的話都說完了,陳坤生對手裡的肉塊突然失去興致般隨手丟在地上,「如果你失去研究的價值,我只好再放一個實驗體進去穆拉薩或者直接抓德魯赫拉,這不是你想看到的吧,既然如此何不好好配合,讓我們彼此都好做事呢。記住,我們都坐在同艘船上,船翻覆了我們還能活,但你只剩死亡這條路可以選。」看似好心建議實質上卻是威脅,陳坤生就是這麼惡劣又自以為風趣的人,隨手甩掉手上的肉塊又往衣服上擦去。
考題已公布,就看考生該怎麼答了。
他愛死這個時刻,主控權在手的感覺美妙到不行。
門緩緩關上,伊森重新閉上眼睛。
又幾個禮拜過去,伊森已經麻木這些實驗,他好想就這樣睡著一覺不醒。
但伊森並沒有真的如此,唯一支撐他睜開眼睛的動力是他們還沒有對穆拉薩伸出魔爪,只要他還有被研究的價值,他們就不會把注意力轉移到霖身上。
自上次陳坤生說那席話後,伊森明白他有價值才能保證穆拉薩的安全,只要他們繼續折磨他,他的那群孩子就還能夠快樂的生活在綠色土地過著屬於他們的人生。
那是我的孩子,每每夜深人靜那些實驗終於消停的時候他都會這樣跟自己說,我要保護我的孩子。
有時念著唸著就這樣陷入沈睡,夢裡偶爾會出現那顆笨笨傻傻的守護樹,用富有力度又溫暖的胸膛將他圈住。
「如果哪天伊森走了,我會把伊森放在古樹,永永遠遠在一起。」
只有這個時候伊森才會難得勾起唇角,霖我相信你,我的生命最後一定會回到你懷裡,就跟穆拉薩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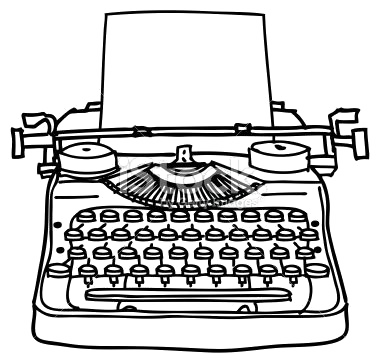
發表留言